果然如周园长所料,再送小东去园里的时候,他虽然也抗拒,但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地址失效发送任意邮件到 Ltxs Ba@gmail.com 获取最新地址
中午的时候温玉老师私发来小东吃饭的视频:“你看小东多顽皮,欺负小暖暖!”
暖暖也是园里和小东一个班上的孩子,比小东小一岁,是个 声
声 气的
气的 娃娃。
娃娃。
视频里小东端坐在餐桌旁,用小脚一下一下踢着暖暖的脚丫,看着暖暖委屈地哼唧,笑得一脸狡黠。
“这家伙,会使坏了!”我哭笑不得地回复。
过了半小时左右,温玉老师又发来视频,小东正和班上比他大一些的硕硕手牵着手躺在小床上准备 睡。
睡。
我突然意识到,小东不排斥和小朋友们亲近了。
这是社 的开始,也是走出自己小世界的开始。
的开始,也是走出自己小世界的开始。
也就是说,小东正在一步一步走出孤独症,他和其他小朋友的互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我惊喜地把这两段视频转发到家庭群里,这绝对是里程碑一般的进步。
姥姥一遍遍循环播放着视频,笑得合不拢嘴:“见效了,这就是见效了!咱家这孩子,会越来越好的!”
果然,傍晚去接小东的时候,周园长向我们反馈:“今天玩得很好,可开心啦!我们的治愈系小帅哥又回来啦!”
小东是园里公认的“帅小伙”,温玉老师曾把工作群消息的截图私发给我,里面清一色是其他地方分园老师们对小东颜值的赞叹:“你们那里有个小帅哥!”“天啊这孩子笑起来太治愈了!”
小东所在的托育园是一家连锁机构,在许多地方都有设立分园。园里的老师会定期在大工作群汇报孩子 况。
况。
小东不知道的是,他的“神颜”已经小有名气了……
再去医院训练的时候,小东的表现好了许多。
负责给他做训练的医生一脸惊奇:“小东进步很大哦!”
训练的效果显而易见。小东听指令的能力比之前有了很大提升,能规规矩矩坐一会儿了。
记得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几个大 按都按不住。
按都按不住。
这才训练了几次,小东已经算是班上比较安稳的孩子了。
其余孩子的家长大声斥骂着自己不安分的孩子,只有我和小东安安稳稳坐在那里。小东不停地被其他家长用来给自家孩子做榜样:“你看 家弟弟,做得比你好多了!”
家弟弟,做得比你好多了!”
我微笑着按照医生的指示辅助小东做动作。
即使小东偶有 绪,我也没有再像之前那样凶
绪,我也没有再像之前那样凶
 地训斥他。
地训斥他。
小东在地上打滚不肯配合,我就去挠他腰间软 ,他痒得咯咯笑着直躲,我便一本正经问他:“还闹不闹了?快起来,不然妈妈还挠痒痒!”
,他痒得咯咯笑着直躲,我便一本正经问他:“还闹不闹了?快起来,不然妈妈还挠痒痒!”
小东不耐烦的时候,我就大声鼓励他:“小东做得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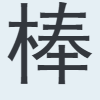 !”“再坚持一下,妈妈就奖励一个大大的抱抱!”
!”“再坚持一下,妈妈就奖励一个大大的抱抱!”
慢慢地,我发现这样耐心的劝导,比声嘶力竭的喝骂有效多了。
于是我和小东这对组合成了课堂上最“另类”的存在。
来训练的孩子大多有孤独症或者多动症等问题,陪同训练的家长即使再有耐心,面对油盐不进如同对牛弹琴的孩子,也会慢慢失去理智。
整个训练室充斥着家长们不耐烦的训斥,还有孩子们委屈的哭声。
小东正一边开心地笑着一边来回跑着套圈。
我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许我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严厉的不通 理的妈妈。我应该做一个温柔的坚定的妈妈,对孩子充满耐心,但同时也要对孩子无理之处坚定地说“不”。
理的妈妈。我应该做一个温柔的坚定的妈妈,对孩子充满耐心,但同时也要对孩子无理之处坚定地说“不”。
这次训练是姥姥和
 陪着。
陪着。
姥姥有事几乎一上午没在医院,而
 也没有进来训练室看一眼。之前和姥姥来训练的时候,姥姥都会找一个小角落偷偷观察训练过程。
也没有进来训练室看一眼。之前和姥姥来训练的时候,姥姥都会找一个小角落偷偷观察训练过程。
姥姥说的那句“叫那么多 来陪着意义不大”似乎立即得到了验证。
来陪着意义不大”似乎立即得到了验证。
本来让 陪着就是想尽量让更多的
陪着就是想尽量让更多的 学习医院的训练方式。
学习医院的训练方式。
不进来看看,来了也是白来,走过场而已。
回去的路上,姥姥开着车,对副驾驶上的
 客气道:“我送你回去吧。”
客气道:“我送你回去吧。”

 忙不迭摆手,给爷爷打了个电话,叫他开车来姥姥家门
忙不迭摆手,给爷爷打了个电话,叫他开车来姥姥家门 接。
接。
一路上两个中年
 家长里短不咸不淡地聊着,也没觉得时间多漫长,就到终点了。
家长里短不咸不淡地聊着,也没觉得时间多漫长,就到终点了。
爷爷果然已经在等着了,接走了
 后,姥姥叹了
后,姥姥叹了 气:“看看都几点了?都知道大中午的赶回来顾不上吃饭,还想不到路上买一点带过来。即便是只给孩子买上饭也行啊。”
气:“看看都几点了?都知道大中午的赶回来顾不上吃饭,还想不到路上买一点带过来。即便是只给孩子买上饭也行啊。”
我看看表,已经快一点了。小东和我们都还没吃饭,更没有午休,下午还要去托育园。
我们三个将就着把早上的冷饭吃了,哄着小东上床睡会儿。
可小东兴奋得很,用姥姥的话说就是“



 声
声 娃娃。
娃娃。  睡。
睡。  的开始,也是走出自己小世界的开始。
的开始,也是走出自己小世界的开始。  况。
况。  按都按不住。
按都按不住。 
 ,他痒得咯咯笑着直躲,我便一本正经问他:“还闹不闹了?快起来,不然妈妈还挠痒痒!”
,他痒得咯咯笑着直躲,我便一本正经问他:“还闹不闹了?快起来,不然妈妈还挠痒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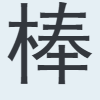 !”“再坚持一下,妈妈就奖励一个大大的抱抱!”
!”“再坚持一下,妈妈就奖励一个大大的抱抱!”  接。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