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本书会很讨厌主 公身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公身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是,这些所有看似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对本我之外的他 而言的相对关系,从他自己的角度去看,却是一种极为负责甚至可以用生命去换取的冒险,是他对自己生命必须完成的体悟。
而言的相对关系,从他自己的角度去看,却是一种极为负责甚至可以用生命去换取的冒险,是他对自己生命必须完成的体悟。
有谁能说他不负责任?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与事 本身相捆绑的虚假的意义,比如高贵优雅的上流生活,体面安稳的工作,
本身相捆绑的虚假的意义,比如高贵优雅的上流生活,体面安稳的工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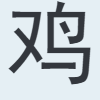 肋般的婚姻。
肋般的婚姻。
而在他的前半生看透这一切之后,就再也无法腐蚀他,也根本无法束缚他了。
那些都是伪装在安宁生活下的平庸和虚假,为了不知名的原因继续着,却可以暗地里摧毁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力,那才是最不道德的事 。
。
直到他有一天听到了灵魂发出的声音,“我必须画画”,那一刻起这就成了他的道德。
为了这个声音,他可以独自承担一切苦难,什么都可以忍耐,把自己的生命完全 给它。
给它。
我想,这就是信仰。
凡是 一生能真正寻获到信仰的,都是有幸。
一生能真正寻获到信仰的,都是有幸。
 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捆绑,只有挣脱,才能通往自由。
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捆绑,只有挣脱,才能通往自由。
挣脱的背后,是一种真正的决然的舍弃。
这一点不是每个 都能做到的。
都能做到的。
我们可以自问一下,如果我们身处于这样的环境,你会舍得放弃一切吗?
会吗?
这是一个高贵的灵魂才拥有的气魄。
所以,那所有其他 因为主
因为主 公而遭受的痛苦甚至死亡,都不要提,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那都是他们自己对某一部分的索取而带来的另一部分的失去。
公而遭受的痛苦甚至死亡,都不要提,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那都是他们自己对某一部分的索取而带来的另一部分的失去。
当然,有得必有失。
这样的一个结局似乎也正是完全符合现实的结局。
有些时候,月亮固然美丽,但是又有几个 真正接触过月亮呢?
真正接触过月亮呢?
这样的一种矛盾,我们不用去说,因为 本身就是矛盾的。
本身就是矛盾的。
这本书不是说教,更像是叩开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虚无的月亮和六个硬币到底是什么。
接着再说到一个寻找。
寻找是一个过程。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地方,希望到达那里就可以使自己解放出来,获得内心的宁静。
他像一个终生跋涉的香客,不停地寻找一座可能并不存在的神庙。
他似乎永远都在他乡,而他想要寻找的却又是一个故乡一般的他乡。
度过了常 看来最痛苦的时期,贫穷,饥饿,嘲笑和不被理解,但庆幸的是,他所拥有的
看来最痛苦的时期,贫穷,饥饿,嘲笑和不被理解,但庆幸的是,他所拥有的 格让他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
格让他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
这种毫不在意一开始就在他身上,如果你还记得一开始他就不愿坐安乐椅而宁愿做板凳。
这种毫不在意,自有它迷 之处。
之处。
它有一种顽皮而坚强的底色,像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世故的成 。
。
到了乡下的时候,那个一亩三分地,是他命中之幸,他终于找到了他的 神家园,这一切都让他安宁,开始了一段美妙而丰盛的本真的创作生活。
神家园,这一切都让他安宁,开始了一段美妙而丰盛的本真的创作生活。
我感觉到那段时间他是最幸福的。
那段时间,他就是一个趴在大地上画画的孩子。
反过来说,他之前经历的那些世俗的冷遇嘲讽、 感的诱惑、生存的艰辛熬煎,这一切也正成就了他的个
感的诱惑、生存的艰辛熬煎,这一切也正成就了他的个 与执着。
与执着。
那些 体和
体和 神历经的磨难,都是必须的。
神历经的磨难,都是必须的。
这才能让他最终找到灵魂的宁静和适合自己艺术气质的氛围,从而实现从自我回归本我的过程。
最后算是回归吧。”
刑学林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是比较感慨的。
他总感觉在做一篇名字叫做自我反省的报告。
“最后是回归。
聆听,挣脱,寻找,回归。
很多 只能走第一步,甚至走不到第二步,因为心里欲念太重。
只能走第一步,甚至走不到第二步,因为心里欲念太重。
但他做到了,他在最后乡下的生活,其实就是回归到了一个生命的起源的状态,那里有他最真挚的感动。
或许最让我感动的应该是在病 膏肓的那个时候。
膏肓的那个时候。
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的那些景象。
那一瞬间,他的铁石心肠似乎被打动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一边一滴,慢慢的从脸颊上流下来。
这一刻,终于让我感受到
 的回归。
的回归。
它不需要多么伟大的意义,这就是温柔朴素的一刻。
在那一刻,他不是什么天才,不是什么画家,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不是痛苦的 体,不是流
体,不是流 的灵魂,他只是想要回到他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土地,他的故乡。
的灵魂,他只是想要回到他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土地,他的故乡。
他的仅此一刻的回归,让我感动不已。
这个视
 为疾病的男
为疾病的男 ,他的心里真的完全不渴望
,他的心里真的完全不渴望 吗?
吗?
 。
。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



 公身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公身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本身相捆绑的虚假的意义,比如高贵优雅的上流生活,体面安稳的工作,
本身相捆绑的虚假的意义,比如高贵优雅的上流生活,体面安稳的工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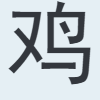 肋般的婚姻。
肋般的婚姻。  给它。
给它。  格让他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
格让他对自己的境遇毫不在意。  神家园,这一切都让他安宁,开始了一段美妙而丰盛的本真的创作生活。
神家园,这一切都让他安宁,开始了一段美妙而丰盛的本真的创作生活。  体和
体和 膏肓的那个时候。
膏肓的那个时候。  的灵魂,他只是想要回到他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土地,他的故乡。
的灵魂,他只是想要回到他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土地,他的故乡。 